

摘 要:对现代国家而言,国家基础性权力有在疆域内放射和渗透的必然要求,管治机制和管治权威是国家基础性权力有机统一的两个面向。港澳地区政治认同差异在本质上是国家基础性权力在两地的程度差异,相应地反映了中央与港澳特区之间管治机制联结程度的差异。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发现,香港和澳门在受殖民统治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管治机制,在回归后重建管治机制时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不同的制度环境不仅带来了中央和港澳地区管治机制的不同整合,也相应地造成了政治认同差异。当前,强化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权威,增进香港对国家的政治认同,需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优势。
关键词:国家基础性权力;全面管治权;管治机制;管治权威;政治认同;历史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1-006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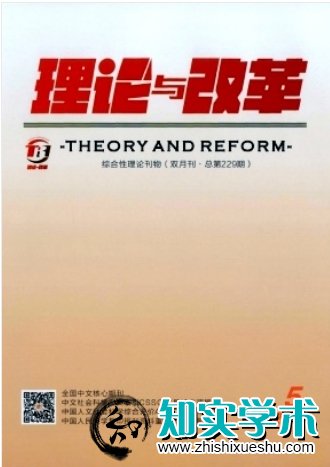
《理论与改革》杂志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全面地宣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和探讨改革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力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回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香港与内地关系在近年来的激荡变化反映了香港的政治认同危机,而同为特别行政区的澳门的政治认同却一直好于香港。如果将“一国两制”的信心、中央政府的信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认同作为政治认同的测量指标,可以发现香港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在回归后第二个十年呈现总体下滑趋势,而澳门却始终处在70%以上。中央政府的信任方面,回归以来香港的均值为39%,而澳门的均值为65%。公民身份认同方面,香港从2007年以来总体呈下降态势,而澳门自回归以来一直稳定处在7~8分的高位 。这不禁引人发问,同样是曾经受殖民统治地区,同样是中央政府设立的特别行政区,回归的时间也几近相同,但为什么两地政治认同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尽管香港的政治认同危机不会对“一国两制”造成结构性冲击,但毋庸置疑会增加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管治成本。2014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首次提出中央全面管治权,表明了中央对基于宪法和基本法的特别行政区管治权力的重视。
由于问题的重要性,关于特别行政区治理的研究在回归后第二个十年间成为显学,而特别行政区的政治认同问题是重要的子议题之一。郭小说和徐海波认为,历史建构出的独特文化、现实中的经济与民生问题和社会中的多元价值取向,是干扰香港政治认同的三个主要原因[1]。这基本反映了三种关于特别行政区政治认同的理论视角。经济与民生问题是其中最基础性的视角,也反映出当前香港管治危机的经济社会根源,然而对为什么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有能力处理好经济与民生的解释在总体上不尽如人意,多数是对政策要求的重复和强调。同时,独特文化、多元价值取向的解释力也有限,其本质都是借用多元主义来对抗具有同质性的政治认同。按照这个逻辑,澳门的政治认同应该越来越糟糕。更何况现代国家只是在私人领域不排斥多元主义认同,但在公共领域则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同质性要求并具有明确的规范[2]。此外,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研究直接将香港与澳门做案例比较的情况还不多见,仅有的比较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冠之以“比较”却只突出一个,主要通过总结与归纳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并以澳门成功范式为标准去想象香港;另一类虽然同时涉及港澳地区,但未能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在实质上仍然是分门别类的论述。鉴于此,本文借助国家基础性权力概念以及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对港澳地区的政治认同差异进行阐释。国家基础性权力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特质,有在疆域内放射与渗透的天然要求,管治机制和管治权威则是其有机统一的两个面向。由于主权和治权的不可分割性,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就意味着国家基础性权力的重新进入,这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港澳地区原有管治机制的“路径依赖”问题。
二、管治权威在港澳地区的流变
现有研究在解释港澳治理问题时,对“一国”和“两制”之间失衡这个底层逻辑有基本共识。陈端洪在研究香港治理问题时,就宪制意义归纳出“一国两制”的宏观分析框架——“对峙”,这既包括政治结构上的,也包括精神价值上的。他认为,一定限度内的“对峙”是合理的,而泛滥的“对峙”则是恶性的;恶性“对峙”是香港政治的病症,具体表现为立宪制干扰和打乱常态政治、广场政治与衙门政治并存[3]。恶性“对峙”本质是一种制度失衡,是“两制”对“一国”的干扰,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建构方面的问题。
(一)国家基础性权力的一体两面:管治机制与管治权威
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国家能力。相较于传统社会,现代国家与社会的联系程度更高,也相应承担了更多的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国家有在疆域内加强对社会渗透和提高管治能力的天然需要,常被用到的概念是“国家基础性权力”。据该概念的首创者迈克尔·曼解释,它是指国家实际能够穿透社会并依靠后勤支持,在其统治疆域内实施政治决策的能力[4]。其实它就是在疆域内放射、控制和规制社会关系的制度能力[5]。由于官僚的职业性和专业性,官僚体系是国家制度性的集中体现,然而官僚体系并不是制度的全部。站在國家的角度,国家基础性权力是政治权力关系由一个中心在疆域内的对外放射,国家对社会的影响需要通过对政党、压力团体等社会力量的控制来实现。因此,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制度性其实是包括官僚体系和其他管治主体在内的一种泛化的管治机制。但是,迈克尔·曼对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探讨更多集中在物质方面,特别是统一货币、交通设置等后勤体系。赵鼎新就此指出,这忽视了人们是否愿意和国家主动合作的问题,也就是“软件基础性权力”,或者说是认受性[6]。站在国家的角度,认受性体现国家的政治权威。而站在社会的角度,认受性体现社会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其实就“软件”而言,亨廷顿很早就将政治权威视作一个有效政府不可或缺的特质[7]。安德烈亚斯·威默在考察国家建构过程时,指出这是一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政治权力交换过程,而政治整合和认同是这个过程的硬币两面[8]。王绍光在研究国家治理时则将基础性权力拓展为8个方面: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国家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吸纳和整合能力[9]。濡化能力就是国家依靠认同感和价值观确立维持社会秩序的方式。
香港特区管治机制和中央管治机制之间联系的脆弱,最终影响到了香港的政治认同。回归以来,旨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工作在香港面临重重困难,引发了多次社会事件,至今仍悬而未决。进入回归后第二个十年,香港的政治认同危机更加凸显。201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拟在中小学推广国民教育为必修科目,但因遭到反对派抗议而不得不暂时搁置。虽然国民教育课本并未退出,但已不能强制推行而改由学校自行酌量。与之相伴随的是,香港的激进本土势力不断崛起,俨然成为建制派与泛民派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势力。一些人甚至依靠煽动极端本土主义当选为立法会议员。
四、结 语
现代国家有在疆域内放射和渗透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必然要求,具体则是管治机制和管治权威放射和渗透的过程。香港和澳门由于一段时期内都脱离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但是它们的相继回归则意味着中央政府管治机制和管治权威在两地的重新建立。港澳地区的制度环境不同,给中央政府管治机制和管治权威的进入带来了不一样的空间。当前,香港和澳门的政治认同差异其实是国家基础性权力在两地权重不同的反映。“一国”与“两制”是本与末、源与流的辩证关系,统一在“一国两制”大框架内。近年来,中央政府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对港澳加强实施全面管治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驳回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自行对基本法的司法解释,昭示了中央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当然中央全面管治权的落实并不意味着对特别行政区自治权的完全否定,在宪法和基本法的保障下,香港依然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利。中央的管治权威和政治认同在香港的巩固始终需要管治机制的紧密联系,这需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优势。这种管治机制一方面要遵循“爱国”这个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组成最广泛的政治联盟。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没有考虑世代变迁对港澳地区政治认同的影响。实际上,近年来在以“激进本土主义”为底色的香港相关事件中,青少年占极大比重。18~29岁的香港青年在所有年龄段中的政治认同最低。对香港政治认同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青年议题的研究,这应该成为一个深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郭小说,徐海波.香港政治国家认同分析与实现机制研究[J].岭南学刊,2017(3):13-19.
[2] René Grotenhuis.Nation-Building as Necessary Effort in Fragile States[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6:110.
[3] 田飞龙.视角:香港回归二十年[M].北京:文津出版社,2017:3-31.
[4] Michael Mann.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its origins,institutions and results[J].Eu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Archives,1984(3):185-213.
[5]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2卷·上[M].陈海宏,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69.
[6] Dingxin Zhao.The Power of Tiananmen[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18-19.
[7]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87.
[8] 安德烈亚斯·威默.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M].叶江,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9:27.
[9] 王绍光.国家治理与基础性国家能力[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8-10.
[10] Hillel Soifer.State Infrastructural Power:Approaches to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J].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8(3):231-251.
[11] Michael Mann.Infrastructural Power Revisited[J].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8(3):355-365.
[12] 暨愛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3):51-56.
[13]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0.
[14] 蔡永军.转型时期的澳门政治精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50-56.
[15] 弗兰克·韦尔什.香港史[M].王皖强,黄亚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5.
[16] 吴志良.澳门政治制度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114-115.
[17] 马志达.论葡澳时期澳门社会治理的法团主义模式[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54-156.
[18] 黄启臣.澳门通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463.
[19] 陆平辉.试论澳门特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建设——纪念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J].学习与探索,2009(6):69-74.
[20] 街总问卷调查显示 逾六成半居民支持国安立法[N].澳门日报,2008-10-25(5).
[21] 刘蜀永.简明香港史:新版[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44.
[22] 刘兆佳.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3-17.
[23] 王凤超.香港政制发展历程:1843—2015[M].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12.
[24] 阎小骏.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4.
[25] 张建.香港建制派:发展逻辑与能力建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3):11-17.
[26] 一群香港公务员就政改方案表决的公开信[N].明报,2015-06-12(19).
[27] 停职!港公务员参与暴动,被扯掉面罩后身份曝光[EB/OL].(2019-09-19)[2019-12-14].http://www.bjd.com.cn/a/201909/19/WS5d8376dbe4b0081bfdf2981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