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互鉴 序进 平行史观 进步史观
先秦儒家的“文野之分”,不免有一种人类文明初始阶段普遍存在的傲慢与自我中心主义的偏见,但在华夏文明的萌发期,中原与周边地区的历时性差异的确存在,尤其是礼乐与礼教,自我中心主义的内核是礼乐中心主义。“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①其实,比较毗邻地区,不管是共时性的别样还是历时性的差异,文明互鉴虽说是一种常态,但古典时期文化交流的流速缓慢,国人尤其是中原地区对域外文化的感知度不高,渴望交流的动因不强,而且这种文化交流大多停留在日常生活层面,在精神层面除了中古时期佛教的输入外,值得数点的内容并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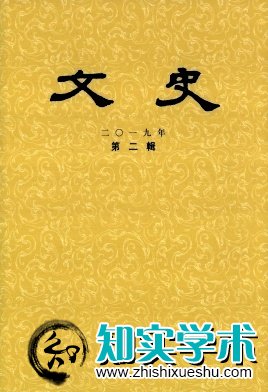
《文史杂志》积极评介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以及优秀文化遗产;向群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普及宣传,进行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启发教育,包含文学,历史,艺术三个范畴。
在漫长的帝国史上,虽不乏中外交流的佳话,但这既没有改变中国人的天下主义观,也没有使人摒弃“文野之分”的思维定势。惟其如此,方能理解为什么鸦片战争时期朝野文书多称西人为“蛮夷”,来自东南方向的“蛮夷”与地处西北的“戎狄”相似,均位居华夏文明之下,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人们普遍凭似是而非的集体记忆来判断真假难辨的“泰西”。随后,沿海地区少数有好奇心的官绅“开眼看世界”,他们虽然是雾里看花,但奇异的观感开始动摇了有识之士对西方的认知。在他们那里,变局观不经意间开始萌动,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行动主义者有感于世局日蹙,未来难料,接续站到了面向未来的历史起跑线上,他们在反躬自问:如何因应难以抗拒的大变局?
一、先秦时期的变易说与帝制时期的守成状
古典时期的中国,知识人有关国运与时局的论述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但也充满张力。中国人的政治“圣经”《周易》所倡导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等时常为后人所乐道。回溯历史,“周邦维新”的确是古典时期一场惊天动地的伟业,以至于600年后孔子发出“郁郁乎哉文吾从周”的心声。西周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黄金时代,颇似西方的雅典,成为人们心驰神往的精神家园。周公之伟大,反衬后人之凡俗,政治领域中的维新或新政并非凡人所能担纲,孔子对周公也只能发出心向往之的赞叹。
西周以降,在政治领域最具革命性变化的是秦王朝。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创制了大一统的官僚帝国,这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周公设计的政治秩序或国家的物理结构。在中原人眼中,地处华夏边陲的秦国有着强悍的军事征服能力,但缺少教化。惟其如此,受传统之约束少,且肆意践踏周礼;更有甚者,公然焚书坑儒,欲斩断西周以来的文脉。秦帝国的短命看似缘于“仁义不施”,其实是遭致文化报复的结果。两汉四百余年,在初始阶段实行郡国并存制,这是对周制的有限妥协,但只是权宜之计,总体上承接了秦始皇设计的帝国体制。更为重要的是汉朝接续并张扬西周以来的文脉,“独尊儒术”,渐渐达到了帝国体制与儒家礼教神奇般的互嵌与深度的融合,实现了秦政与儒学的双赢,从而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秦汉之制或秦政遂成为中国人心目中一个不朽的政体。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① 毛泽东认为“百代都行秦政法”。② 笃信进步主义史观的黑格尔则认为中华帝国“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成为非历史的历史”。③ 從大历史观的角度观之,秦汉以降历史进步主义已经退场。
在帝制时期,秦汉之制堪称完美,这在很大程度上屏蔽了中国人的政治想象力与制度创新力。然而,完美的秦汉之制并不能确保万世一系,王朝循环也是中国人的政治常识,但这个常识暗含的“变易”已不再是“维新”,而是王朝的“周期律”。所谓改朝换代,改的只是姓氏,换的只是驾驭秦政之人,而非制度。第一个明确提出“易制”的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他在改朝(驱除鞑虏)换代(恢复中华)之外第一次加上了“易制”(创立合众政府),④且要毕其功于一役。
在自秦政创制至孙中山明确提出“易制”的两千余年里,间或出现过为挽救王朝危机的变法,但鲜有成功者,更无名垂青史的变法巨人。更有甚者,在后人的集体记忆中,变法者往往被人怀疑是自不量力,有关变法的叙事与其说是令人豪情万丈,不如说是令人厌倦,从而形成了一个不宽容变法的政治文化。
如此,在中国文化中虽然有着丰富的变易思想,但在政治实践中呈现出来的是对现状的守护。每当变法或新政作为一个政治议题提出后,抗拒变法之声往往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最为守成者所乐道的就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⑤抽象的“道”被守成者演绎成具体的秦政。诚如费正清在论及王安石变法时所言:“官僚和文人对变法的反对基本上不可能是阶级利益的不同,这更深刻地反映了一个官僚国家行政上天然的惰性———更趋于守成不变,自此以后这成为中国政府的特征。”⑥在帝制时期,守成几乎是一种常态。
二、“互鉴”观的生成及其内在的张力
所谓“互鉴”,指在中国人的视野与价值天平上,承认一个“他者”的存在,并可以与“我”相互借鉴,不再死守天下主义及礼教中心主义,对中国人来说,这无异于发生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虽说是革命,但并非一蹴而就。承认互鉴的认知基础是鸦片战争以来累积起来的变局观,所谓变局是指对世局的认知。说到变局,最为后人乐道的是1872年中兴名臣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①
此言一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胫而走。事实上,从全球史的角度观之,“大变局”的来临并非始于李鸿章时代,早在17世纪就生成了。史景迁认为,自1600年,“中国在与他国竞逐稀有资源,从事贸易往来,扩展知识时,其命运已与其他国家休戚相关。”②中国人对大变局的认知当然不可能出现在1600年,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因为知识所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③ 当然对大变局的感知也非延宕到李鸿章时代。
鸦片战争前后,身处粤闽前线的官绅已感知到这一非同寻常的变。魏源的贡献不在于发现夷有长技,而是心服口服地承认其有长技,并大胆说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夷夏之辨”与“文野之分”的颠覆。目击1841年的吴淞战役的黄钧宰认为,英法之洋人“乃自中华西北,环海而至东南,梯琛航赆,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④
1860年前后变局升级。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京、设立总理衙门、他国在京设立使馆、接受条约体系等,中国进入了不可逆的开放主义时代。对此,中国人的认知与情感复杂而多元,但在法理与事实上“他者”已得到承认,变局遂成为朝野使用的高频词语。1864年,专注于时局变化的王韬说:“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⑤1865年,李鸿章深知:“外夷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⑥同年薛福成说:“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⑦1867年,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在奏稿中说:“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⑧
变局观的生成一方面承接古典时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变易说,另一方面论者更关注具有特殊意义且难以抗拒的“他者”,两者的结合便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行动主义者。所谓行动主义者大致有两种人:一是贡献智慧,二是身体力行,更多是兼而有之。他们的认知和行为取向就是中西互鉴,互鉴的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体西用,最为乐道者是张之洞,⑨但此论之生成与变局观如影随行。魏源的“长技论”开其端绪,而形成一种格式化的表达句式则出自李鸿章的智囊冯桂芬,“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瑏瑠此后围绕这一句式而展开的讨论甚多,诸如“本末论”“道器说”“主辅说”。1895年《万国公报》的主笔沈毓桂撰文:“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瑏瑡三年后,张之洞发表了著名的《劝学篇》,力主“中体西用”,该词遂成为人们乐道一时的口号。
从历史观的角度观之,“体用论”其实是一种含糊的平行史观。中西文明各有源流,“互有得失”,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但在接受体用论的阵营里,论者的侧重点有异,或者说体用论是一个充满张力与变数的命题,有着较大的言述空间。有的人强调体的价值至高无上,值得骄傲,甚至认为用既不重要,也不迫切。“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①有人强调用的功效巨大无比,且十分迫切。“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②更多如张之洞,强调体用不可偏废。“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③这是一种调和论者。
变局论者的不同言说,预示“中体西用”只是一种脆弱的共识,内在的分歧与日俱增。若作历时性的观察,在19世纪的后40年,随着西学东渐的速率加快,在器物、制度、文化及人员往来方面的交流不断加深,中国人从初始阶段在情感上对互鉴说难以接受,渐渐转换成接受西强中弱的事实,1860年代以后,“夷务”渐渐被“洋务”所取代,进而有“洋货”与“土货”之分。土洋二分的思维与原先的互鉴说之间的张力在放大,在不经意间“平行论”逐步被“强弱论”所替代。于是乎,甚至有人认为西方有自己的“体”,“师夷之长技”应在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展开。1876年,驻英使臣郭嵩焘将自己的观感记录在日记中:“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④1884年10月26日,淮军的重要将领、历任江苏巡抚和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口授《遗折》,直言西方“自有本末”“具有体用”:
近岁以来,士大夫渐明外交,言洋务,筹海防,中外同声矣。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⑤
时值中法战争,作为身处战争前线的封疆大吏,要比内地的官绅更加了解敌情,对知己知彼的思考与观察更加深刻。该“遗折”其实是对冯桂芬以来的互鉴说提出质疑。1860年以来,国人大都信奉体(纲常名教)用(富强之术)二分的思维,前者无疑包含了帝制中国的制度。张氏事实上提出了新的三分法:礼乐教化-议院学校-轮船大炮。西人虽然在禮乐教化方面“远逊中华”,但在议院、学校(政治制度)方面“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议院、学校应视为西方独有的“体”,同样值得中国人借鉴。不幸的是,开展了20余年的自强运动是“遗其体而求其用”,如此下去,中国将“不足恃欤”!如果说冯氏等人信奉“政教一体”,那么张氏则主张“政教二分”;“西政”就是“西体”,其与轮船大炮互为牵引,缺一不可,这是一种新的“西体西用”说。此论虽然勉强维系互鉴格局或平行史观的论政思维,但承认“西体”就是对既有的中体西用的突破,它不仅暗含了西强中弱的现状,从趋势来看,播下了进步主义史观的种子。
张氏对“遗其体而求其用”的批评,未必是言人之未言,但确是言人之所不敢言。一个体制内的封疆大吏,胆敢挑战王朝的政治底线,发出如此不合时宜的言论,并不表示今上像唐太宗那样开明,其用遗折的方式来表达,恰恰说明专断体制下言路之狭窄。是年,摄政的西太后看了该折后有何感想不得而知,可知的是遗折并没有给王朝奉行的中体西用战略带来什么显著的变化,互鉴观退场的时刻尚未到来。
三、“序进”观的生成及其爆炸性的影响
观念的进场与退场,不同于发生在某一时刻的政体变更,而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大体说来这一过程的展开是从精英到民众,从沿海到内地。生活于沿海的精英是观念变更的主要推手。如此,可以发现一些重要人物在某一时刻的作品对观念变化产生的深刻影响。
新观念的产生大多有赖于经验性观察与思考,而突发的重大历史事件更加易于催生具有革命性的观念,并有助于新观念的传播。鸦片战争之于师夷、五四运动之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均系显例,而对序进论之认知发生影响最大的就是甲午战争。
甲午前30余年的自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中体西用的有效性或互鉴的成就。中国建成了亚洲首屈一指的舰队,现代工业体系(军用与民用、重工业与轻工业、交通与通讯等)尽管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高,区域分布不均,但门类日趋完备,经济增速与财税增长显而易见。但处在进步主义时代,民族国家纷纷登上了国家主义的田径场,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除了跟过往比较外,更重要的是跟赛场上的竞争对手比拼。
甲午战争“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夢”。所谓“大梦”即大错!错在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及中体西用说。西方之强盛,“用”是表,“体”是里;中国之积弱,不只是“用”,关键是“体”。甲午战争的结局对国人心理的冲击远甚于咸同年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说李鸿章的“变局说”催生了体用论及互鉴论,那么梁启超的“大梦说”则催生了历史进步主义及序进论。如今,所有的国家被排成了一个从野蛮到文明、落后到先进的序列。中国由天朝上国坠落到野蛮的位置,且面临弱肉强食的现实。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①
甲午以后,前所未有的焦虑与恐慌在全社会蔓延,这是一个迫切需要开出一剂速效处方的时代,更需要有人来论证处方的有效性,以便对上面提到“三种人”进行启蒙,使其变成积极的行动主义者。
严复是关注西方富强之源的孤独的先行者,虽然《天演论》到1898年才出版,但其进步主义历史观之形成可追溯到留学英国时期。1895年2月,他发表的《论世变之亟》首倡历史进步主义的观念,加之其后发表的数篇政论文,严复成了“大梦”的唤醒者,是康德意义上的启蒙运动中的“别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②
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也。即如今日中倭之眐难,究所由来,夫岂一朝一夕之故也哉!③
“世变”“运会”“天时”,表达的是世局在变,历史发展有着不可抗拒的趋势与定律,但中国人的认知是错误的:“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④ 此论无异于宣布秦以来的循环史观在认知上是狭隘的,历史周期律的成见应该退场,必须承认“日进无疆”的进步主义具有普适性。
严复接下来大谈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尔,“天演”“进化”取代了“世变”。从进化论的角度审之,中国“民力已絍,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⑤显然,与李鸿章之辈基于体用观来因应大变局不同,严复则是基于进步主义史观来解释“世变”。西方的强盛,“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⑥ 中西有别,绝非你有“用”,我有“体”,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用,处在不同的序列,差别在于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文明。
严复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下笔斟字酌句,典雅古朴,对读者的学术积累要求甚高,使其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知识界产生爆炸性影响的是梁启超。“笔端常带情感”的梁启超虽说是康有为的精神之子,但其思想上的成年礼是在严复主持下完成的。1897年3月,严复给在上海任《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写了一封长达21页的信,批评其一些错误而浅薄的言论。梁启超复信道:“循环往复诵十数过,不忍释手”。“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非有先生之言,则启超堕落之期益近矣。”①梁氏非常认同严复的天演论,认为中国与西方是“先后”之异,“暮旦”之别,是一种历时性的差异。
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亦当丕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此又不易之理也。②
受到进化论思想洗礼的梁启超,不仅赋予康有为托古改制的三世说以进步主义的意涵,“天演之事,始于胚胎,终于成体”,而且依据进步主义史观,绘就了中国人政治上的行动路线图。
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③
梁启超将人类政体的演变次序分为“三世六别”,有着对严复思想的误读之嫌。该文也引用了严复的一段话:“欧洲政制,向分三种:曰满那弃(君主)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时(贵族)者,世族贵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谟格拉时(民主)者,国民为政之制也。”④这其实是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各城邦政体所作的共时性归纳。每种政体又有所谓“正宗”与“变态”之分,合起来有六种。梁启超将严复的进化论、康有为的三世大同说及有限的西政知识揉合到一起,编造出了一个“三世六别”政体演进轨迹,其政治目的是为变法维新提供依据与目标。一旦把秦政嵌入到了“三世六别”的序列之中,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尚在君主之世,下一级当升至“君民共主之世”(即君主立宪)。梁启超还武断地宣称:“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这是将严复的进化论推向极端化,陷入了机械的一元论的历史观。
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为“东学”所倾倒,进一步从学理上强化他的政体进化论,为君主立宪大造舆论。
世界之政體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者十数,除俄罗斯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馀各国则皆君主立宪政体也。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君主专制政体,朝廷之视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盗贼;民之畏朝廷如狱吏,而其嫉之如仇雠。故其民极苦,而其君与大臣亦极危,如彼俄罗斯者,虽有虎狼之威于一时,而其国中实杌陧而不可终日也。是故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⑤
经由庚子之变,中国人对亡国灭种的担忧更甚。如果说《时务报》时期梁启超的“三世六别”说带来的社会反响是有限的,那么,《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简约明了的三种政体拾级而上,使朝野有识之士为之折服。随后,在新式媒体及封疆大吏的奏折中,速行立宪成了关键词,立宪遂成为20世纪初的强势话语。
四、何以因应序列:“循序”抑或“躐等”?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大增,在舆论场上,东京与上海、上海与内地,桴鼓相应,政见纷呈。“但是在对现状的分析上,各持不同的未来图景的论者之间,其意见却奇妙地一致。这就是将从秦始皇开始到20世纪初延绵不绝的中国的政治体制都一并视为专制政体。”①当中国政体的历史坐标勘定后,在未来中国建立何种政体的议题上,出现了“循序”与“躐等”两种主张。梁启超出于对君宪救国论的痴狂,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三种政体嵌入进化-天演论,②臆断出一个三种政体“次序井然”的命题。中国“必当先经立宪君主,而后可成立宪民主,乃合进化之次序也”。③ 力量聚合起来的革命派则主张民主共和,论战由此展开。论辩双方尽管政见对立,但都以进化论为理论支点。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④
孙中山也是进化论、天演论的膺服者。
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⑤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痛斥中国“不能躐等而为共和”之说“反进化之公理”。“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语曰:‘取法于上,仅得其中。择其中而取法之,是岂智者所为耶?”⑥
孙中山强调,不应该被动地理解与接受天演论。“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等;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此说亦谬,于修筑铁路可以知之矣。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继渐改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汽车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车乎?于此取譬,是非较然矣。
在梁启超看来,孙中山的“铁路汽车之喻”混淆了技术进步与社会变革的差别,是对进化论的误读。“两者原不相蒙也,若乃铁路汽车之喻,则真闻所未闻也。夫所谓良也,恶也,本属抽象的观念,非具体的观念。语政体之良恶,而离夫‘人与‘地与‘时三者,而漫然曰:孰为良,孰为恶,此梦呓之言也。”⑧
孙中山虽然反对不能“躐等”,但他的革命方略也有严格的“次序”:第一期为军法之治(3年),第二期为约法之治(6年),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应“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⑨ 从这个意义上讲,孙中山是一位选择性的序进论者。
孙、梁围绕未来中国出路的论战,一旦从天演、进化、次序之争转入异族统治中国有无正当性后,“革命排满”“革命必剖清人种”⑩ 的口号很快在气势上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在大变局时代,民族主义易受情感支配,而政体之构建则需要理性。武昌起义爆发后,康有为还在喋喋不休地发出不合时宜的忠告:“为治有序,进化有级,苟不审其序,而欲躐级为之,未有不颠蹶者也。”瑏瑡从历史进程来看,清亡民兴,革命派凯旋,亚洲第一共和国诞生在中华大地。站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孙中山感到欣慰,康、梁心存隐忧。“二次革命”以后的历史走势表明,康、梁的隐忧并非多余,孙中山的欣慰未免天真。其后孙中山的“训政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康、梁“断难躐等”的妥协。
五、讨论:进步主义之接受:观念抑或工具
西方古典时期,“学者大多囿于一种恶性怪圈:他们认为人类围绕一系列发展阶段循环往复,这些学者之中仅有少数例外。”①中世纪的基督教化使人普遍产生原罪感,生命不过是走向天堂或地狱的一个序曲。16世纪以来,随着商业、科技发明、启蒙运动的展开,西方社会才从这一循环和基督教时代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进步观念开始萌生。
人类进步的观念是一种理论,涉及一种对过去的假设和对未来的预言。它的基础是对历史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认为人类是朝着一个确定和理想的方向缓慢前进———即一步一步地前进,并推断这一进步将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②
19世纪前后,受进步观念的支配,思想家转而探索人类社会进步的轨迹。马克思追随进步时代的脚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17世纪以降,资产阶级创造了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而且要将旧世界改造成新世界。任何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必须接受由旧世界转向新世界的现实,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进步、进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进步主义几乎被奉为圭臬。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自然界的演化及技术的突破是不同的。“历史也不仅仅是自然中的演化过程的延续。如果思想并非自然过程的结果,而是前提,那么即可以由此断言,以思想为其特征和引导力量的历史则属一种不同自然王国的观念类型,因而也需要做出不同的阐释。由此,出现了历史哲学。
严复在输入天演、进化等观念时,“倾向于用‘天演译,以自然界为对象;用‘进化以人类社会为对象。”⑤与“天演”相关联的概念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进化”相关联的概念有“立宪”“自由”“民主”等。
诚如梁启超所言,观念的移植不同于“铁路汽车之喻”。萨义德认为,观念的旅行方式需要经历四个步骤。
第一,需要有一个源点或者类似源点的东西,即观念赖以在其中生发并进入话语的一系列发轫的境况。第二,当观念从以前某一点移向它将在其中重新凸显的另一时空时,需要有一段横向距离,一条穿过形形色色语境压力的途径。第三,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姑且可以把它们称之为接受条件,或者,作为接受的必然部分,把它们称之为各种抵抗条件———然后,这一系列条件再去面对这种移植过来的理论或观念,使之可能引进或者得到容忍,而无论它看起来可能多么地不相容。第四,现在全部(或者部分)得到容纳(或者融合)的观念,就在一个新的时空里由它的新用途、新位置使之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了。⑥
改变人类认知的观念总是复杂而理性的。观念传播过程中的变异未必仅存在于跨文化之间,在同一文化内部也同样存在。严复在分析“世变”的时候,大谈中国与西方在历史意识、政治观念上的差异;在剖析“原强”时,关注“群学”及“民力”“民智”“民德”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不备而生民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①
严复虽然对历史意识作了复杂性的阐述,但他并没有充分讨论天演、进化与进步主义的不同意涵及适用范围。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很容易将其统称为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进步主义。中国人接触到天演论、进化论后,进而将其约化为进步的观念,固然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之虞有关,不进步就成为“弱肉”,这是“天择”,更重要的是与梁启超的文字鼓动相关联。对多数读者来说,细细品读《天演论》远非一般识字者所能企及,而报章上梁启超的时务文体,不仅通俗易懂,且带来立竿见影的快感与共鸣。
梁启超从《时务报》时期鼓吹“群学”“学会”“学校”,到《新民丛报》时期的“新民说”,显然有着对严复思想的接续与阐发,但梁氏的言论是为其政纲服务的。为了实现其政纲,他不惜将观念工具化。无论是“三世六别”,还是三种政体演化说,均在用天演论的思维来论证政体变化的次序,这与严复对天演、进化的理解已发生了萨义德所讲的“某种程度的改变”。
严复与梁启超都是知识人。严复总是在深思熟虑地琢磨字词与意涵的吻合,“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而梁启超在奋笔疾书,大量生产精神快餐。严复力求小心表达,精确无误;梁启超总想语不惊人死不休。湖北一知縣读到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文章后如痴如醉:“快读鸿篇,无美不备。有时崇论宏议,倾海翻江;有时丽句清词,排珠缀玉;纵横九万,上下五千。为国家二百余年开此风气,于天下五大洲内判其纲条,腴若餐花,洞若观火,令人服膺永佩。”②严复所提供的观念产品,到了梁启超那里便成了朗朗上口的“丽句清词”,极具复杂性的观念变成了易懂而肤浅的政治逻辑。如是,钱穆批评梁氏的政体序列说:“何以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洋学者此等分类之外?不知此等分类,在彼亦仅为一时流行之说而已。”③在钱穆眼里,梁启超不过是治史之“宣传派”。梁启超也承认20世纪初“专以宣传为业”
孙中山是那个时代最具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情怀的政治人物,长期的域外生活经历,使他内心对落后的中国与发达的西方充满紧张与焦虑,振兴中华是其发自内心的宏愿,其使命与担当意识较康、梁更加强烈,为了革命排满,民主共和,其对天演、进化作“某种程度的改变”自在情理之中。
概而言之,从冯桂芬的“主辅说”到张之洞的“体用论”,意在论证借鉴西方富强之术的正当性,这是对世局的片面性理解;梁启超与孙中山虽有“循序”与“躐等”之争,但皆用“天演”“进化”来强化君主立宪或共和革命的正当性,这当是对严复思想的选择性误读。严复在输入进化论时大体是传承了英国的社会中心主义和社会有机体论的思想传统,而梁启超与孙中山(尤其是孙中山)在接受进化论时则转向了政体中心主义,相信政体万能。凡此,反映了清末民初政治人物理论武库内的利器是有限的。诚如康有为所言,他们受“感情”支配,缺少“通达之深识”,⑤乃是这个时代政治人物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