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一带一路 政权更迭 模式识别 影响分析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20)03-0097-17
【DOI编号】10.13851/j.cnki.gjzw.202003006
《北京党史》办刊宗旨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刊登党史研究成果,提供历史资料,开展宣传教育,以史为鉴、资政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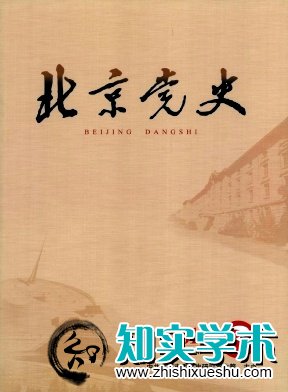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沿线国家[①] 可能的政权更迭已成为影响建设推进的重要问题。政权更迭形式多样,原因复杂,包括經济、政治和国际因素等。国家现代化、经济危机、政治制度不匹配、国际环境与外部干预等因素都可能引发政权更迭。[②]政权更迭造成的影响同样复杂。主流观点多认为政权更迭易引发破坏性影响,而在经济社会条件不成熟的国家强行推动政权更迭,也易引发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崩溃。但是,政权更迭也可能在某些条件下促进国家发展。[③]在“一带一路”研究中,有关政权更迭的研究涉及沿线国家的国情、外交风险预警、项目投资保护等多个方面,[④]这些都是影响项目持续推进的重要因素。
本文从系统和整体的视角分析政权更迭对可持续的“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既有研究多聚焦某一具体的政权更迭形式,本文拟弥补这一缺陷,以整体方式,并适当扩大政权更迭的外延,将选举革命等纳入研究内容。从政权更迭的暴力程度和制度化程度两个维度,可将政权更迭分为两大类三种形式,即颠覆性政权更迭与常规性政权更迭两大类,其中颠覆性政权更迭中又分和平与暴力两种形式。颠覆性政权更迭主要包括反叛、内战、颜色革命等非法并直接摧毁旧制度的夺权模式,而常规性政权更迭则指在选举等名义上符合规范的夺权方式。
本文主要分析两大问题,一是总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的基本模式与规律,二是分析这些国家政权更迭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分析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⑤]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模式
按照颠覆性政权更迭与常规性政权更迭的分类,本文基于13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权更迭基本分布情况,[⑥] 将其分为发生颠覆性政权更迭的国家、发生常规性政权更迭的国家和未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
(一)基于类型划分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权更迭分析
颠覆性政权更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属小概率事件,但呈现反复性特征。常规性政权更迭属于大概率事件,发生频率极高,但可预测性更强。在统计时间段内未发生任何政权更迭的国家则具有明显的制度性特征。
第一,发生颠覆性政权更迭的国家。[⑦]2001—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有15个国家至少出现一次以上的颠覆性政权更迭,占所统计国家总数的14%。此类政权更迭通常伴随暴力或大规模抗议活动,并造成国家体制和政府权力格局的彻底变更。[⑧] 另有统计数据显示,有10个沿线国家在2001—2017年期间经历过两次或两次以上非正常政权更迭,其中后一次政权更迭通常与前一次政权更迭带来的破坏性效应有关。这说明颠覆性政权更迭具有一定的反复性。[⑨] 但是需指出的是,颠覆性政权更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属于小概率事件,未发生此类事件的国家占所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数量的近4/5。
进入21世纪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现的政权更迭方式多样。在“颜色革命”、内战和政变等常见的颠覆性政权更迭模式中,“颜色革命”占25%,政变占47%,内战占20%,外部干预占8%。其中,内战属于暴力政权更迭模式,通常会彻底破坏一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而“颜色革命”的暴力程度则相对较低,通常只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骚乱;政变则介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暴力性,但相比内战则相对缓和。由外部干预而导致政权更迭的概率相对较低,以上三种政权更迭模式均为颠覆性政权更迭,其不仅导致政治权威的更替,而且对所有投资与国际经贸合作均会造成巨大影响。
第二,发生常规性政权更迭的国家。[⑩]相对于颠覆性政权更迭模式占政权更迭的两成多,常规性政权更迭则占七成以上,后者更具一般性和普遍性。此外,连续出现多次常规性政权更迭国家比例也明显上升,高达54%。笔者选取其中出现常规性政权更迭次数最多的10个国家,发现这些国家除了瓦努阿图(8次,第一位)属于发展中国家之外,其他多为较发达并实行多党制政体的国家,其中大多位于欧洲地区。[11] 这些沿线国家在政治体制上通常实行定期选举,因此导致此类政权更迭呈现反复的特征。[12]
第三,未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这类国家共有24个,可分为三类。第一类通常由某一主导性政党长期执政,[13]包括越南劳动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这类国家的政府通常拥有较强的合法性基础和治理能力,因而政权更迭风险较低。第二类国家多为传统君主制国家,如摩洛哥、沙特阿拉伯等。此类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受到传统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影响,多为一元君主制,政权轮替通常由领导人的自然更替实现,因而出现政权更迭概率也相对较低。第三类国家则多为一些领导人超长期执政的国家,[14]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政体特征,如津巴布韦时任总统穆加贝、阿尔及利亚时任总统布特弗利卡等。这些国家领导人的超长期执政,使其国家在长时期内未出现任何形式的政权更迭。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所选取的数据库数据更新截至2017年,有部分国家在随后的两年内出现了政权更迭。例如,阿尔及利亚时任总统布特弗利卡和津巴布韦时任总统穆加贝都在2017年后被迫下台,这表明长期未发生任何形式政权更迭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其政体安全稳定,反而可能意味着其发生政权更迭的风险已逐步积累到临界点。因此对于此类国家,尚需结合其具体治理模式进行具体分析。
(二)基于空间维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分析
数据分析表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颠覆性政权更迭风险高发国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西亚、北非地区的政权更迭现象尤为明显。自进入21世纪以来,西亚、北非地区有近一半国家出现颠覆性政权更迭。其更迭形式多样,包括外部干预、“颜色革命”、内战和军事政变等。政权更迭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不稳定。除西亚、北非地区之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欧中亚地区也成为颠覆式政权更迭发生频率较高的地区,上述两个地区分别有24%和26%的国家出现政权更迭。[15] 在东欧、中亚地区至今仍面临苏联解体后发展转型的艰巨任务,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在西方政治的影响下,常成为“颜色革命”的高发地区。相比之下,亚太、拉美和西欧地区出现颠覆性政权更迭的比例相对较低,分别为15%、6%和0。
在常规性政权更迭中,空间分布呈现出与颠覆性政权更迭完全不同的模式。一方面,此类政权更迭更为普遍,在世界各地区都频繁发生,明显高于颠覆性政权更迭发生的频率,与颠覆性政权更迭的区域分布也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常规性政权更迭与颠覆性政权更迭之间表现出一定程度此消彼长的现象。在颠覆性政权更迭发生率为0的欧洲地区,其发生常规性政权更迭的概率是100%,即所有欧盟国家在2001—2017年间都发生了至少一次政权更迭。而在发生颠覆性政权更迭频率最高的中东地区,其发生政府更替的比率反而在所有地区中处于最低位(57%),即有43%的中东国家在2001—2017年间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政权更迭。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仅次于西亚、北非的颠覆式政权更迭的高发地区,但该地区常规性政权更迭发生频率在世界范围内则处于低位(64%),有约35%的撒哈拉以南“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家在2001—2017年间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政权更迭。一国政权更迭发生频率的高低并不能直接反映该国的整体稳定与发展情况,出现多次常规性政权更迭国家也不意味着其长期处于不稳定或发展停滞的状态,而长期未出现任何政权更迭的国家也并不意味着该国政治安全风险较低,反而可能说明该国政治风险被长期遏制,存在潜在爆发的风险。
(三)基于时间维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分布
從时间维度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的情况,有助于更好地引入相关政治发展和历史因素,更全面展现相关国家的政治制度变革。基于数据可得性和研究便利,笔者将研究的时间跨度设定为1946—2017年,以年为单位记录不同年份出现政权更迭的平均数。此外,笔者还统计了四种不同形式的政权更迭(革命、内战、政变和选举)在不同年份的平均数。
经过分析,常规性政权更迭在时间分布上呈现明显的周期性,部分年份是此类政权更迭的高发年份,平均4—5年就出现一次常规性政权更迭的高发期。而其他年份出现常规性政权更迭的比例则相对较低。这说明常规性政权更迭正逐步制度化,成为很多国家的正常现象(见图1)。
颠覆性政权更迭也在相应时间范围内具有明显的波动性特征,而此特性也与既有政治学理论相符。既有理论多认为政权更迭的发生具有周期性特征,并以浪潮式呈现。[17]当一国出现颠覆性政权更迭时,也会促使其他与之相似的国家发生政权更迭,形成“雪崩效应”。[18]自二战结束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遭遇了多次颠覆性政权更迭的高发期,并分别对应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苏联解体以及2003年以来“颜色革命”等重大国际事件。
不同类型的政权更迭在时间轴上差异化分布(见图2)。1946—2017年,政变发生的频率整体上高于内战与“颜色革命”。有国外学者认为,在一国国内的政治风险中,统治阶级“身边人”背叛的风险概率更高。[19]因此,相比于其他形式的颠覆性政权更迭,政变在一段时间内是最常见的形式。“颜色革命”与内战大多分布在时间轴的右端,近20年才呈现出波浪式上升势头,而政变发生频率则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这说明颠覆性政权更迭的主导模式正发生变化,“颜色革命”与内战的发生频率总体有所上升。[20]
二、政权更迭产生的影响
政权更迭产生的影响具有多重性,本文将主要从全局性与涉我性两个角度切入。一方面,政权更迭将对当事国的整体发展带来显著影响,可能改变该国进一步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外部宏观环境。另一方面,政权更迭也可能直接影响中国对外投资和“一带一路”建设。笔者采取定量研究与案例讨论相结合的方式,以包括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政权更迭以及其他治理指标在内的面板数据集(Panel Dataset)为基础,使用分析面板数据常用的固定效应模型,就政权更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发展和中国与相关国家经济合作进行量化分析。此外,本文还通过案例进一步分析政权更迭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影响。
(一)面板数据分析
通过搜集相关数据,可建立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集,其中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中国对外投资、政体况、人口、脆弱国家指数、腐败指数等内容(见表1)。
第二,以泰国与马来西亚为案例分析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与相关国家国内政治冲突牵扯程度所产生的影响。泰国和马来西亚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国家,这两个国家在近6年内均发生了政权更迭或政府轮替。2014年,泰国爆发政变,英拉政府下台,这是一次典型的军人政变导致政权更迭的事件。2018年,马来西亚也发生政权更迭,执政长达61年之久的巫统在选举中意外失利。虽然巫统下台是在合法大选的形式下进行,但其实质上已经构成一次较为典型的“选举革命”。在形式上,這两次政权更迭总体上都以和平方式进行,政权更迭后的初期都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和“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了一定负面冲击。但从最终影响来看,泰国2014年的军事政变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而马来西亚2018年的政权更迭对“一带一路”建设一度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冲击。
在泰国军事政变爆发后,中国对泰国的投资流量出现明显下降。从政变爆发前2014年的8.34亿美元下降到政变爆发后2015年的4.07亿美元。泰国新政府执政后,立即宣布将暂停并重新审查上一届政府所签署的2万亿泰铢以上的大型基础设施。中国与上一届政府签署的高铁协定也受到影响。但是除了初期的震荡外,泰国军事政变对中泰经贸合作冲击有限。并在经历了2015年的回调后,中国对泰国的投资总额上升至11.12亿美元,而中泰高铁等重点项目也恢复合作。[33]
马来西亚的政权更迭则对双方在“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2018年8月宣布,将取消三个中资企业在马来西亚投资建设的大型基建项目。这些项目由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承建,均被视为中国在马来西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项目,这些项目的暂停引发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对“一带一路”项目在马来西亚的推进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也被西方媒体炒作为“中国遭遇挫败”。
泰国与马来西亚发生的政权更迭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冲击、影响不同。出现差异的关键在于中国在两国的合作项目与该国内部政治斗争的关联度不同。在泰国发生政变后,与中国的合作项目并不牵涉其国内政治斗争,且被政权更迭后上台的新政府普遍视为有利于其巩固执政地位。因为加强与中国经济合作可助其取得国家发展成就,巩固合法性。同时,由于泰国2014年政变后遭到美国与欧盟的打压,而中国却秉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使得泰国新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华合作。因此,中国与泰国“一带一路”合作项目非但没有遭遇其内部政变的冲击,反而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加强。而在马来西亚,中国的合作项目则涉及其国内政治的两个矛盾点。一是马来西亚国内民族问题。马哈蒂尔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观念,担心中国资本会使马来西亚华人势力坐大,影响其国内政局,这导致马哈蒂尔对上一届政府与中国签订的大型合作项目十分警惕。二是马来西亚新政府对中马合作项目可能带来的债务问题也存在担忧。这些因素导致中马数个“一带一路”项目成为马来西亚国内政治斗争的靶标,进而限制了新政府继续与中国开展合作的积极性。不过,随着交流的深入,马来西亚新政府也逐步深化了对中国的认识,而且中方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也使合作项目逐步与马来西亚国内政治“脱敏”,因此马来西亚目前已经恢复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合作。
三、特点归纳和风险应对
政权更迭是“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在发生时间、分布空间、发生国家类型和影响等方面的表现各有特点,中国必须要有效应对。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的特点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政权更迭在发生时间上呈现周期性特征,其中社会运动配合选举制度产生的“选举革命”已经成为主流,并可能成为长期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灰犀牛事件”。内战、政变、“颜色革命”等颠覆性政权更迭频率相对较低,属于“黑天鹅事件”,但也存在突然密集爆发的可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实行一定程度的竞争性选举制度,这使相关国家的反对派可利用选举发动所谓“选举革命”,将民粹主义与社会运动和选举活动相结合,导致在选举周期出现意外结果,并在新政府执政后清算上一届政府推动的项目。数据分析表明,此类政权更迭的风险将长期存在并可能周期性爆发。相对而言,内战、政变、“颜色革命”等颠覆性政权更迭模式出现的频率相对较低,但此类事件也存在周期性高发的特征,并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东南欧的“颜色革命”,还是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以及2019年在阿尔及利亚和苏丹出现的政权更迭,都具有突发性和聚集性相结合的特点,而且在某一国家率先出现的颠覆性政权更迭会在短时间内扩散到其他国家。
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权更迭在地理分布上与区域发展及稳定水平具有对应关系,颠覆性政权更迭与常规性政权更迭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颠覆性政权更迭高发于国内冲突严重、治理能力不足的西亚和非洲地区,而在治理水平相对良好的欧洲、东亚、拉美等地区则发生的频率较低。常规性政权更迭则呈现相反趋势,在治理水平较高地区的频率显著高于西亚和非洲等地区。这说明以上两类政权更迭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颠覆性政权更迭多为一国治理出现严重问题,国家内部矛盾激化的反应;常规性政权更迭虽体现了对当时政府执政的不满,但也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基本治理制度化与国家政权运作的有序化。
第三,两类国家具有颠覆性政权更迭相对较高的风险。一是在历史上出现多次政权更迭的国家,二是在相当长时间内未发生政权更迭但存在严重政治僵化现象的国家。根据前文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出现颠覆性政权更迭的国家可能具有两种看似完全相反的特性。第一类是在历史上频繁出现颠覆性政权更迭的国家,其具有反复性。有关数据分析已发现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权更迭具有这一特点。例如,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连续发生“颜色革命”,泰国连续出现军人政变等。一个国家如果在相当长时间内周期性出现颠覆性政权更迭,这通常说明该国存在难以化解的结构性矛盾,需要不定时通过最激烈的方式爆发。另一类则属于长期内未爆发颠覆性政权更迭,但存在严重的政治僵化问题的国家,这些国家会在某一时刻以“黑天鹅方式”出现政权更迭。例如,阿尔及利亚、津巴布韦等国都是因为这一因素导致在2017年后发生颠覆性政权更迭。此类国家通常国内治理制度不健全,执政党内部制度建设也不完善,进而导致政权与个别家族和个人紧密结合。这类所谓“家族独裁”式政权(Personalistic Regime)虽可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稳定,但也会因领导人健康、“宫廷政变”等出现颠覆性政权更迭。
第四,政權更迭在短期内对“一带一路”项目建设通常会带来负面冲击,但其长期影响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政权更迭的暴力程度与新政权能否恢复国家秩序,二是“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与该国政治竞争的关联程度。政权更迭是一国内部矛盾和社会不满的集中爆发,因此必然导致政局动荡、发展受阻,并会对中国与某些前政府签订的重大或特大项目造成负面影响。但如果政权更迭对该国基本发展态势和基础设施建设冲击程度有限,新政权能够迅速恢复秩序,提供有效治理,则相关合作项目依然有较大可能得以恢复。此外,政权更迭是一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其对外部经济合作的影响取决于国际经济合作与该国内部斗争的关联程度。如果中国的相关合作项目并不涉及其国内政治利益纠葛,则不会成为政权更迭中的焦点,也可规避负面影响。
(二)风险应对策略
第一,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研究,密切关注其政权更迭风险,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预警模型,提前预判该国发生政权更迭的风险,并对其产生形式与暴力程度进行预判。应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闭环式政权更迭风险研判机制,密切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将其纳入中国海外投资保护和“一带一路”可持续推进的总体框架中进行统筹考虑。在进行“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和长期项目建设前,充分考虑该国总体政权稳定程度,并做好出现政权更迭时的预案,确保项目可持续性。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也要及时关注所在国的政局是否稳定,并做好社会公关与沟通工作,确保相关项目所在国多数主要政治团体的知晓与理解。如项目进行过程中出现政权更迭,应根据预案及时调整对策。在确保中方项目人员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在该国恢复项目合作。
第二,针对不同类型的政权更迭,需分类设计预案并建立灵活反应机制。针对具有重大暴力性质的政权更迭,应及时安排项目人员撤回,确保相关人员生命安全。针对暴力性质较低的政权更迭,则应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适当留守,观察形势,在政权更迭后第一时间与新政权建立联系,主动维护国家与项目利益。
第三,在确定“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时,要密切注意项目合规性与项目在所在国社会的接受程度,避免项目卷入有关国家的政治纷争。争取建立合作项目与对象国社会团体和反对党派的协商对接机制,缩小项目利益攸关方的排他性,扩大包容性。进而在一旦发生政权更迭时,也能确保有效应对,避免出现项目完全中止的最坏结果。同时要尽可能采取符合国际规范的项目合作模式,在合同确立阶段将各种风险应对予以法律化,一旦出现政权更迭导致项目受损的情况,可以依法按照合同止损。
第四,应在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前提下创造性介入,在顶层设计上化解政权更迭的风险。一方面,中国应继续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这可使中国避免在相关国家发生政权更迭时被迫选边站队。另一方面,中国也应加强与相关国家政府和社会各主要势力的全方位沟通协作,从而在当事国一旦发生政权更迭时,有效保障中国的海外利益。
[责任编辑:杨 立]
[①] “一带一路”建设提出初期包含欧亚大陆的65个国家,但近年来实际已远超这一范围。因此本文也在原有65国基础上将范围扩大为与我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国家,截至2020年1月底,中国已经同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具体名单可参考中国一带一路网:《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https://www.yidaiyilu.gov.cn/gbjg/gbgk/77073.htm。
[②]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 1959, pp. 69-105; Jack A. Goldstone, et al., “A Global Model for Forecasting Political Instability,”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4, No. 1, 2010, pp. 190-208; and Gunitsky, Seva. “From Shocks to Waves: 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8, No. 3, 2014, pp. 561-597.
[③] Daron Acemoglu, et al., “The Consequences of Radical Reform: The French Revolu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1, December 2011, pp. 3286-3307; and Richard N. Haass, “Regime Change and Its Limits,”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4, July-August, 2005, pp. 66-78.
[④] 李世杰等:《政治风险影响我国直接投资“一带一路”国家的实证分析》,《江淮论坛》2019年第6期,第127—133页;刘海猛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综合评估及防控》,《地理研究》2019年第12期,第2966—2984页。
[⑤] 在具体研究方式上,本文将采取定量研究为主,辅以案例分析的方式。以与政权更迭有关的数据库为基础,结合案例进行分析。这一类数据库主要包括威尔第·迪约尔(Vilde Lunnan Djuve)等人于2019年提出的政权更迭数据库,政治制度数据库和政治动荡分析小组提供的数据。威尔第·迪约尔数据库:Vilde Lunnan Djuve, Carl Henrik Knutsen, and Tore Wig, “Patterns of Regime Breakdown Since the French Revolution,”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October 2019, p. 5;政治制度数据库:Carlos Scartascini, Cesi Cruz, and Philip Keefer, “The 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2017 (DPI2017),” 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dataset /wps2283-database-political-institutions; Political Instability Task Force, “PITF State Failure Problem Set, 1955-2018,” 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crdata.html。
[⑥] 笔者区分发生颠覆性政权更迭国家、发生常规性政权更迭国家和未发生政权更迭国家,并考虑到政权更迭的影响时间,统计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进入21世纪以来(2001—2017)年出现的政权更迭情况,进而分析其形式、空间和时间分布。
[⑦] 此部分数据来源为Vilde Lunnan Djuve, Carl Henrik Knutsen, and Tore Wig. “Patterns of Regime Breakdown Since the French Revolution”。
[⑧] 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阿拉伯之春或201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
[⑨] 例如也门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后连续出现三次政权更迭,埃及在2011年后出现两次政权更迭、吉尔吉斯斯坦也经历了两次政权更迭。
[⑩] 此部分数据来为政治制度数据库,Carlos Scartascini, Cesi Cruz, and Philip Keefer, “The 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2017 (DPI2017)”。
[11] 包括意大利(5次)、斯洛文尼亚(5次)、希腊(5次)、拉脱维亚(5次)、捷克(5次)、韩国(4次)等。此数据表明,常规政权更迭是比颠覆性政权更迭更为频繁和常见的政治现象。
[12] 以意大利为例,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先后在2001、2006、2008、2013、2018年举行了五次全国性选举,在每次选举中平均有10多个政党组成4—5个政党联盟进行竞争。并且伴随2018年以来“五星运动”的发展,在传统左翼和右翼的政党竞争中再添民粹主义新政党,政党斗争形势进一步复杂化,政府通常难由稳定的多数政党组成,政权更迭频繁。《新闻分析:意大利大选牵动欧洲》,新华网,2018年3月2日,http://www. xinhuanet.com/world/2018-03/02/c_1122480210.htm。
[13] 主导型政党国家还包括安哥拉(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古巴(古巴共产党)、莫桑比克(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老挝(老挝人民革命党)、卢旺达(卢旺达爱国阵线)。
[14] 此类政体还包括: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刚果(布)、吉布提、阿尔及利亚、乍得、塔吉克斯坦、津巴布韦等。
[15] 撒哈拉以南非洲多为经济欠发达国家,国家基本制度和社会结构还不成熟,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族群矛盾等发展问题。以上因素都促使了该地区许多国家易出现颠覆性的政权更迭。
[16] 政治制度数据库,Carlos Scartascini, Cesi Cruz, and Philip Keefer, “The Databa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2017 (DPI2017)”。
[17] Seva Gunitsky, “From Shocks to Waves: 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8, No. 3, 2014, p. 562.
[18] Henry E. Hale, “Regime Change Cascades: What We Have Learned from the 1848 Revolutions to the 2011 Arab Uprising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2013, pp. 331-353.
[19] Milan Svolik, “Authoritarian Reversal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2. No. 2, 2008; and Milan Svolik,The Polit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0] 参见金良祥:《中东:礼崩乐坏之下亟需重塑主权原则》,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2020年1月6日,http://www.siis.org.cn/Research/Info/4840。
[21] 本文所采用的拟合曲线依靠局部加权回归方式进行拟合,可以更好反映数据变化拐点和趋势。具体参考:longgb123:《[算法]局部加权回归(Lowess)》,2018年3月11日,https://blog.csdn.net/longgb123/article/details/79520982.
[22] Vilde Lunnan Djuve, Carl Henrik Knutsen, and Tore Wig. “Patterns of Regime Breakdown Since the French Revolution.”
[23] Fragile States Index, https://fragilestatesindex.org/excel/.
[24] Monty G. Marshall, Ted Robert Gurr, and Keith Jaggers, “POLITY? IV PROJECT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1800-2018,” https://www.systemicpeace.org /polity /polity4.htm.
[25] 世界银行开放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
[26] 模型1:经济增长率it= γit+颠覆性政体更迭* xit+脆弱国家指数* xit+政体4民主程度* xit+人口数量* xit+人均GDP* xit+μit 。模型2:经济增长率it= γit+常规性政体更迭* xit+脆弱国家指数* xit+政体4民主程度* xit+人口数量* xit+人均GDP* xit+μit 。模型3:中國对外投资流量it= γit+常规性政体更迭* xit+脆弱国家指数* xit+政体4民主程度* xit+人口数量* xit+人均GDP* xit+μit。模型4:中国对外投资存量it= γit+常规性政体更迭* xit+脆弱国家指数* xit+政体4民主程度* xit+人口数量* xit+人均GDP* xit+μit。
[27] 定量分析部分所指的显著关系均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关系。
[28] Caroline Freund, “Regime Change, Democracy, and Growth,”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pril 2014,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regime -change-democracy-and-growth.
[29] 环亚经济数据库,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
[30] 同上。
[31] 《中国同埃及的关系》,外交部网站,2019年11月更新,参见https://www. 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
[32] “中国同利比亚关系”,外交部网站,2019年12月更新,https://www.fmprc.gov.cn /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8018/sbgx_678022/t6306.shtml。
[33] 刘馨元:《中泰重启“大米换高铁” 机遇与挑战并存》,广西大学网站,2015年4月5日,http://cari.gxu.edu.cn/info/1087/6465.htm。